导语:行政协议较之于民事协议,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行政机关享有单方优益权。
虽然自从行政协议类案件被明文纳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内以后,行政优益权这一词汇频频被提起,但一直以来,行政优益权的概念及运行仅限于学术讨论中,而没有统一明确的相关规范。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的规定,我们可以将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界定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为了避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享有单方变更和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力。
但在具体的行政协议个案中,行政优益权究竟应当如何运作,仍存在较多争议亟需廓清,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则是厘清行政优益权的范围。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的宋静律师,由于业务范围大多集中在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争议(招投标程序、土地出让金纠纷、招商引资等),这些诉讼动辄上亿元、或者都与政府各个部门产生多方联系,不仅仅是简单看法条,就能搞定的。
本文旨在给法官或律师提供识别行政优益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
一、行政优益权识别的必要性
为什么需要讨论行政优益权的范围?
主要基于部分裁判观点认为,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这就需要在个案中甄别行政机关的行为究竟是否属于行使优益权,进而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程序审查标准。
部分判决观点提出,行政机关单方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相对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解除前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参见林茂惠诉苍南县人民政府解除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8911号),部分判决更是直陈,行政协议的变更应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参见李海兰等12位与兰考县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公告协议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1110号)。
这些裁判观点提出的,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使单方优益权,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在变更或解除协议之前,必须听取行政相对方意见的裁判模式,经由互联网自媒体的转发,迅速被扩散,引起各地法院纷纷效仿。
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永远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选择题的最佳答案就是尽可能兼顾。
行政机关在管理过程中,既要讲究效率,又要兼顾公平。
讲究效率,需要缩短办案期限,简化办案流程,精简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避免被动重复处置。
兼顾公平,就要走足行政程序,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查明案件事实,客观作出裁断。
行政机关在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过程中,必须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势必会延长办案期限,耗费行政资源,耽误行政效率。
如果行政机关行使单方优益权的范围未能厘清,行政机关优益权范围的被不当扩大,势必导致行政机关不得不在程序上花去更多的成本,造成管理效率延缓的两难境地。
因此,准确界定行政优益权的范围,对于简化行政程序,确保管理效率至关重要。
二、行政优益权识别的困境
目前,尚没有文献或者裁判观点给我们提供系统的,在行政协议中识别行政优益权的标准。
即便了解了行政优益权的概念,我们仍无法完全解决优益权范围辨识的困难。
(一)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给行政优益权的识别造成困难
行政优益权的范围对于行政机关如何行使优益权的影响如此重大,但其边界和疆域却模糊不清。
或许有人认为行政优益权的范围不言而喻——从行政优益权的概念出发,行政机关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单方变更协议的行为均属于行政优益权的行使。
但何谓“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本身属于不确定的概念,在具体的个案解释中,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唐仕国和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变更纠纷”((2018)最高法行申8980号)案中,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关岭县政府)因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唐仕国所有的房屋负一层的用途错误认定为经营面积,导致补偿款多算。
关岭县政府作出《关于对被征收人唐仕国征收补偿协议变更的行政决定书》,责令唐仕国退回多领取的补偿款部分。
对于关岭县政府的责令退回决定如何看待,原一、二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就出现了分歧。
原一、二审法院认为关岭县政府的责令退回决定属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行使优益权,单方变更协议的行为,再审法院则认为,即使经营性用房的面积认定有误,关岭县政府可能会多支出一部分补偿款,但仅以多支出一部分补偿款,不能据此认定关岭县政府可以给予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征收补偿协议。
行政机关多支出征收补偿款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受损,再审法院和原一、二审法院的看法不一,直观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给行政优益权辨识带来的困难。
(二)行政协议中的合同行为和优益权区分存在困难
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既是合同当事人,有权行使合同权利,同时又是执法机关,有权在法定情形下行使行政权力,这就造成了行政机关的行为在行政协议中究竟应当界定为合同行为,还是行政优益权的困惑。
如在“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诉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中,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草本工房公司)和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荆州开发区管委会)签署了《招商项目投资合同》,草本工房公司受让荆州市289.5亩土地并投资开发,后因草本工房公司土地闲置,荆州开发区管委会对草本工房公司发出《合同自行终止通知书》,要求终止前述《招商项目投资合同》。
关于荆州开发区管委会单方终止《招商项目投资合同》这一行政协议的行为,原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属于荆州开发区管委会行使单方优益权的行为,最高法院再审则认为,荆州开发区管委会的终止协议行为仍属于原《合同法》框架内的行为,并非基于行政优益权。
再审法院和原一、二审法院的认定大相径庭,根本分歧就在于行政优益权的范围边界较为模糊,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的识别标准。
(三)行政协议中行政优益权和行政处分行为易于混淆
我们偶然可以遇到在行政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甚至在履行完毕之后,行政机关又行使相关行政职权,要求行政相对人(原行政协议当事人)履行和原行政协议相关的义务。
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行政协议典型案例中的第10个案例,即“成都某商贸有限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决定案”。
该案中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成都某商贸公司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履行产生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经民事诉讼判决后,驳回了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转而向成都某商贸公司作出温国土资发(2018)366号《决定书》,以作出行政决定的方式决定对某商贸公司追缴民事诉讼中未予支持的违约金。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决定书》的方式追收违约金,是否属于行使行政优益权?
相关的案例分析皆未作出判断,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行为,不得而知。
三、行政协议中的优益权识别之我见
通过上述部分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并不是只要行政机关单方提出变更或解除行政协议,就属于行使行政优益权。
面对具体个案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情形,如何在行政协议中准确识别行政优益权的行使,我们需要划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行政优益权的范围不能过于宽泛,避免把本不属于优益权的行为包括进来,耽误行政效率。
行政优益权的范围不能过窄,否则起不到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因此,确定行政优益权的标准,需要对行政效率和社会公平之前找到一个平衡点。行政优益权的标准还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作为分类和精拣的标尺,不具有实操性起不到作用。
因此,确定行政优益权的标准,还需要充分了解行政优益权的构成要素,以及对行政协议案件中的特殊情形有所预判。
最高院在“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诉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中对行政优益权的要素有精辟的论述。
该裁判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应当受到4个方面的限制。
1、行使行政优益权必须出于防止或除去对公共利益的重大危害;
2、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必须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作出释明;
3、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4、应当对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优益权的行使造成的损失依法或者依约给予补偿。
上述4方面的限制,实质上是从操作层面对行政优益权的构成要素作了分解。参考行政优益权的上述要素要求,我们认为,行政优益权的识别,应当从以下情形中具体区分:
第一,行政机关如果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违约行为或不适宜继续履行协议的行为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行政机关作出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不属于行政优益权的行使。
原因在于,行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行政相对人一方,行政机关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无需向行政相对人予以补偿,不符合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补偿行政相对人损失的构成要素要求。
第二,如果行政机关可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的适用情形在行政协议中双方已有约定的,即便行政机关是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也不建议将其归属于行政优益权,而建议在民事合同的框架内解决争议。
理由在于,如果行政协议中对于行政机关有权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协议的情形作了具体规定,说明协议双方对于可能出现的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情形已有预判。
一旦约定的情形出现,行政机关变更或者解除协议无须再履行听取行政相对人申述申辩意见的程序,既保障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又不至于因程序缺失影响公平。
第三,如果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协议,而行政机关变更或者解除协议的情形在协议中又未订明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解除协议的行为属于行使行政优益权的情形。如果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应予补偿。
第四,行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非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对出于公共利益的原因无法充分释明的,则不符合行政优益权的构成要素,不属于行使行政优益权的情形,由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而不是补偿责任。
对于上述标准,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所以笔者主张,行政机关即便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单方变更或解除协议的情形,只要在行政协议中事先已有约定,就不建议将其划入行政优益权的疆域,主要原因仍在于考虑到“公共利益”范围解释的不确定性,避免行政优益权过分扩大,反而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所以在此作了限缩的解释。
同时也需要再次强调,对于上述情形中凡涉及到公共利益因素的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必须在个案中对公共利益的前提作出充分的论证,以赢得行政相对人的信服和人民法院的认可,确保行政协议的有序履行。
更多的行政优益权争议,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中向大家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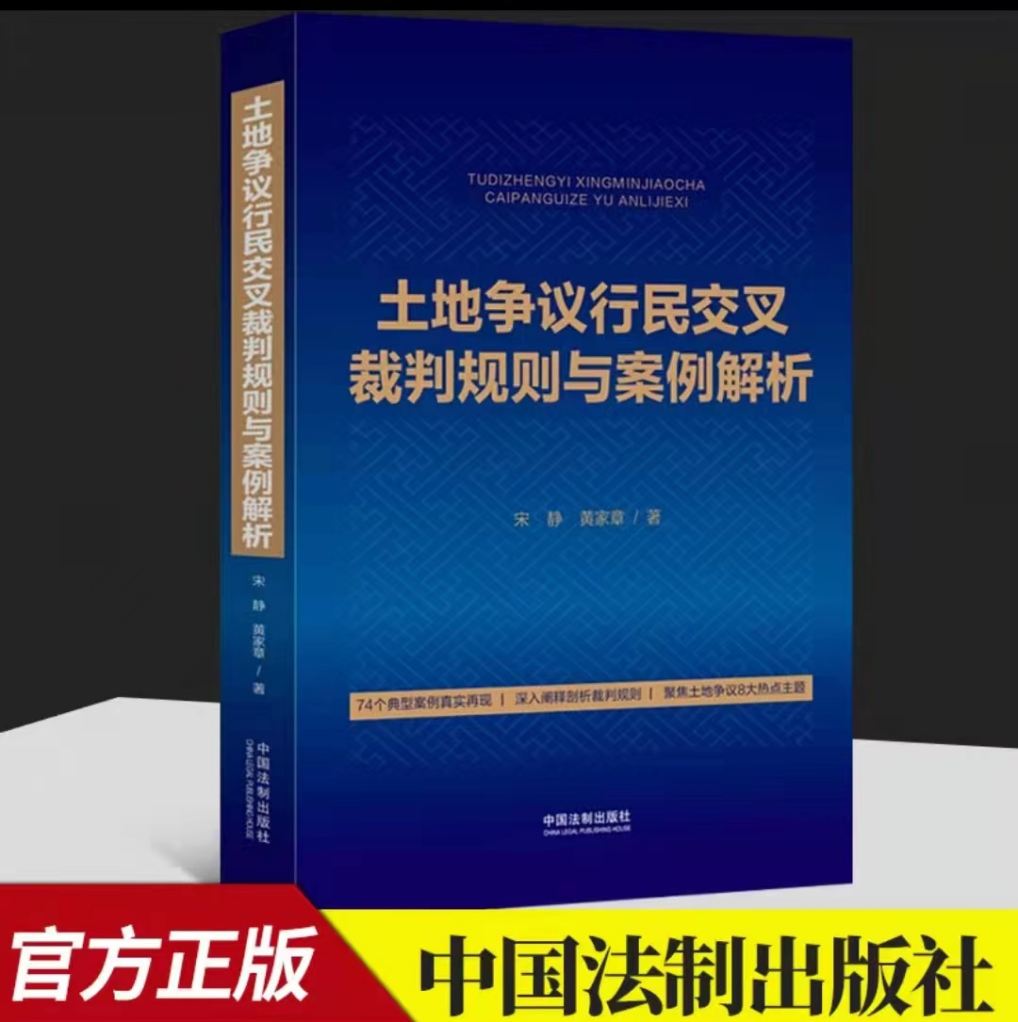
宋静律师的这本新书《土地争议行民交叉裁判规则与案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历经3年筹备,2年动笔,前后5年共撰写了第一稿60万字。应出版社要求,正式出版删减至30万字。本书囊括了读者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权利从“生”到“死”(从“取得”到“注销或收回”)的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配有典型案例。该书实属宋静律师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是宋静律师从事重大复杂土地诉讼,特别是行民交叉诉讼领域多年耕耘的集大成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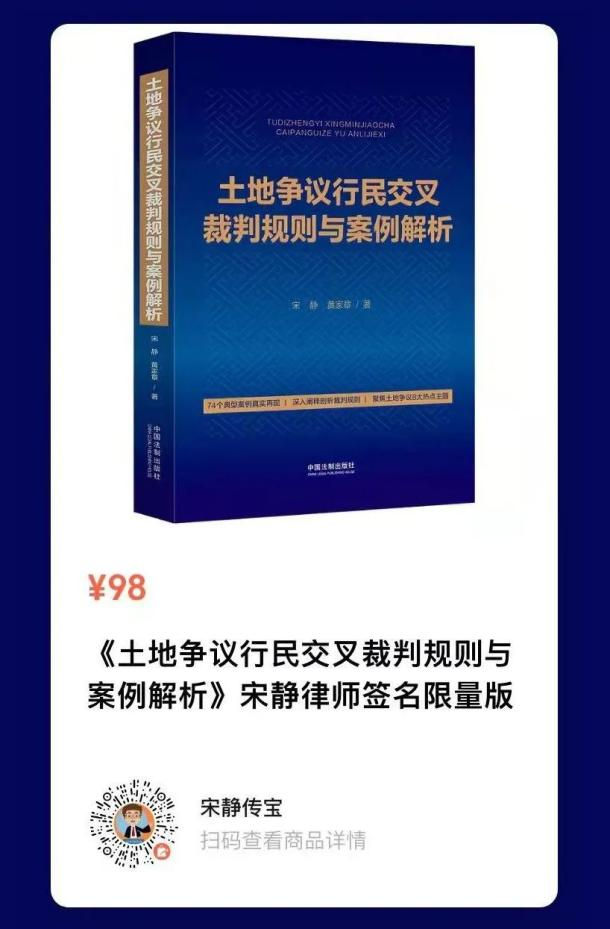
目前,该书正在各地的新华书店、京东、当当等平台火热销售中。
供 稿 | 宋静律师团队
排 版 | 董丽娜
审 定 | 石伟民





